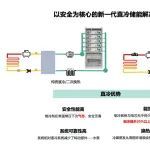高原礦區的冬天
從青海回到河南老家已經五年,我卻時常想起高原礦區的冬天,還有木里山那肆意的北風。
高原礦區的冬天來得特別早。每年十月,中原大地還是金秋正濃、碩果飄香的時候,這里就進入了冬季。十二月時,這里已是寒冬。
最先感知冬天到來的是木里山的小草,昨天還是綠茵茵、脆生生的,一場寒風吹來,頓時改了顏色,變成一地金黃。但這金黃也只是瞬間的,或一兩天,或三五天,就完成了從秋天到冬天的過渡。傍晚的時候,起風了,不一會兒,竟飄起了雪花。最初是一絲一絲的,如煙似絮。漸漸地,風大了起來,雪花也密了起來,打著旋兒,一會兒呈順時針,一會兒呈逆時針。不大工夫,地上就積了厚厚的一層。天越來越暗,礦區的漢子都鉆進了宿舍。風不知什么時候停了,雪也不知什么時候停了。第二天,太陽出來了,大地一片白茫茫的,地上的積雪漸漸融化。人們驚奇地發現,昨天的一地金黃變成了一地枯黃,沒有一絲光澤。
能讓人感知冬天到來的,還有木里山的風。就在頭一天,它還柔柔綿綿的。一夜之間,這風就像川劇變臉一樣改了面孔,變得猙獰起來。一見到人,它就像螞蟥見了血,直往人的骨頭縫里鉆。挖煤的漢子不傻,臨出門的時候,早把略顯單薄的秋裝脫去,換上厚厚的棉衣,有的還戴上雷鋒帽和厚厚的口罩。他們走在風里,伸伸胳膊,舒展舒展腰背,好像在說:“風啊,你使勁兒刮吧,我不怕你。”
木里山的冬天,是風的季節。有風的日子十之六七。有時剛剛還晴空萬里的天空,忽然一陣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聲音在耳邊穿過,接下來就出現風那強勁而野蠻的身影。一時間,天昏地暗,日月無光,地上的落葉、塵土等都飛了起來。就連礦部大院花圃里的枯黃野草也嚇得擠在一起,哆嗦著身體。風越來越大,就像有一雙無形的手在使勁蹂躪著這片天空,簡直要把屋頂掀起來,三五米外便視物不清。窗戶外電線桿上的電線在風中一張一弛,發出凄厲的哨聲。
不知過了多久,風停了下來,萬籟俱寂,時間也好像停止了。
這時,你走出門外,只能看到一片灰蒙蒙的天空。剛才的一切似乎是一場夢。
木里山的冬天,風是常有的,雪是不常有的。
木里山的冬天,室外溫度通常在零下二十攝氏度以下,夜間最低可達到零下四十攝氏度。一個平常的冬日,天突然變了,先是刮了整整一上午的風。下午,風小了,雪花帶著冬日的祝福從天而降,剛開始是細細的、密密的。漸漸地,雪越來越大。不一會兒,屋頂上,草地上,礦部后面的山坡上,全都成了銀色的世界,顯得神秘又圣潔。
天晴了,雪停了,一片白云飄了過來。
從礦部大門遠眺,不遠處的祁連山若隱若現,在冬日陽光的照耀下分外美麗。往后看,礦部后面的山坡上,有的地方雪厚,有的地方雪薄。快日落的時候,微黃的陽光照耀在山腰上,那點雪好像忽然害了羞,微微露出點粉色來。
在這里,我要說一下木里山的積雪。在河南老家,不論下多大的雪,過不了幾天,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在老家,還有一句俗話,“下雪不冷,化雪冷”。但木里山的雪卻并不這樣——雪落到地上,常常一個多月都不會融化。盡管木里山的冬天很少下雪,卻時常能看到四處殘留的積雪。
木里山的雪下在地上,風一吹,腳一踩,甚至踢上一腳,雪還是雪,只不過換一個地方繼續存在。這一點,和高原礦工一樣:不論在什么地方,不論條件多么艱苦,他們從不叫苦,總能扎下根來。
青藏高原上,天是那么藍,云是那么白。不遠處的祁連雪山腳下,臥著一兩頂帳篷。一旁的布哈河像一條玉帶般蜿蜒而去,一個騎著馬的牧民,或是一個頂著紅頭巾的藏族女子,趕著一群羊在河邊放牧。這場景,真像一幅水墨畫。
高原礦區的冬天,如果只有大風和積雪,倒也尋常。最妙的是太陽雪。瞧,雪正下著,太陽卻出來了。它先是輕輕撥開厚厚的云層一角,試探般地露出一點臉來,接著再露一些,最后索性探出整個身子,天空隨之明亮起來。請閉上眼想:冬日的陽光下,雪花漫天飛舞,是怎樣一番動人的景象。
作者:王曉峰版面編輯:袁理
編輯
來源:中國煤炭報
聲明:本文系轉載自互聯網,請讀者僅作參考,并自行核實相關內容。若對該稿件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質疑,請立即與鐵甲網聯系,本網將迅速給您回應并做處理,再次感謝您的閱讀與關注。
不想錯過新鮮資訊?
微信"掃一掃"